教皇· 伶人
Submitted by kzeng on Thu, 2011-09-01 10:00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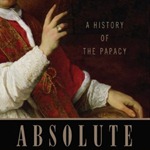
前阵子早上挤地铁的时候一直在看 Absolute Monarchs: A History of the Papacy,从 Android 的 Google Book 上下载的免费预览,只能看前四章。被这本书的名字吸引主要是因为 Perry Anderson 的巨著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。Absolutism 的兴起是欧洲 17 到 18 世纪的事情了,所以很好奇可以追溯到公元初的教皇如何是 absolute monarch。但是就能免费读到的四章而言,没有任何关于 absolutism 的讨论, 倒是有教皇和教会的不少八卦,譬如早期教会的某位长老(presbyter)是一名太监,同时还掌管着罗马皇帝康茂德(Commodus)的后宫。当然也有一些其它比较有趣的事情,譬如在基督教的早期,东部教会关于教义曾有数次比较大的辩论,而此时以罗马为中心的西部教会却并未积极参与(例如第一次尼西亚会议),除了地理上原因外,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拉丁文语言词汇不如希腊文那么丰富,许多语言上的细微差别无法在拉丁文中体现出来。
可能原来是学外交的缘故,对于这类语言的细微差异总是很感兴趣,因为对于国家而言,语言上的细微差别可能是一场战争的诱因之一,譬如鸦片战争。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缔结的《中英天津条约》,其中第五十一款:
嗣后各式公文,无论京外,内叙大英国官民,自不得提书夷字。
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所著的 The Clash of Empires: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对于“夷”字翻译导致的中英冲突有详细的考证。“夷”字的英译,该在 foreigner 与 barbarian 之间,但是英语中无法用一个词准确的与“夷”对等以至于后来简单的把夷与 barbarian 划上等号,导致争端不断(当然这也不纯粹是翻译的问题,古语云,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)。其实,如果“夷”字是 barbarian 的话,那么《孟子·离娄》中的这句话该怎么翻译?
孟子曰:“舜生于诸冯,迁于负夏,卒于鸣条,东夷之人也。文王生于岐周,卒于毕郢,西夷之人也。
不仅是在过去,即便是现在,仍有这样的问题,记得原来上课时仔细讨论过公报中 recognize 和 acknowledge 的差别,两者翻译成汉语都可以翻成“承认”,但是英语本身的差异就消失了。
然后免费的前四章就读完了,由于保持着念博士时的“优良传统”—— 只看书不买书 (可惜现在没有图书馆了),所以“专制”教皇的故事就只能读到公元六世纪末的 Gregory the Great 。
然后只能翻手机上的存书。所以又翻开了章诒和的《伶人往事》,因为这是一本很不错的地铁读本,故事都比较短(除了马连良那一章),适合10分钟时间的阅读,有始有终。以前读过几遍,注意的多是八卦掌故等叙述性的部分,这次再读,仔细看了作者的一些议论。
既是“往事”,所以感慨大多怀旧,或者厚古薄今。前后翻阅,又觉得作者逻辑难以自洽,比如她感慨现在的剧坛处处可见官、商的影子,但是旧时代的剧坛又何尝不是?其实作者应该乐见官、商捧出来的剧坛(就像四大名旦之所以成为四大名旦与背后捧的人密不可分一样),因为她本人是不喜欢“人民的剧坛”的(建国后对于戏剧文化的一系列改革)。
又好比作者感慨现在没有堪比旧时代的戏剧大家了,其实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—— 说明普通人的选择多了,不必被某种职业所禁锢。要知道倡、优与隶、卒在古代都是地位远低于士农工商的贱民(也就是入贱籍的人),往往世代相传,不能变更,出身乐户,就不得不作一辈子的乐工倡优。所以身隶贱籍,唯一能有所改变的,就只有做好一行,以希望能得到上层人士的青睐(譬如唐明皇,李后主,后唐庄宗这样的人物)。后来虽然雍正帝“开豁为良”,革除了各地贱籍,令其改业为良,但是正如《伶人往事》中所记录的,很多人其实也只有到了走投无路才去做伶人,因为社会习惯上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。倘使程砚秋有别的选择,估计他也不一定再选择梨园行,就像程砚秋成名后发誓不让自己的儿女再入学戏一样——后来也确实如此,程砚秋三子一女,没有一人入梨园。当然确实也有人完全是因为兴趣而唱戏的,譬如过去的那些票友们,但是不同之处仍然是在于这些人是有选择的。所以人们能选择是否演戏是一件好事,像程砚秋这样被棒打出来名角儿,不要也罢(程砚秋在出师前腿就被师父打伤,后来一直到他到欧洲考察戏剧时,才由德国医生手术治好)。
虽然不很赞同作者的一些议论,但是她的叙述部分还是很好看的。特别是一些小掌故,譬如一位叫做陈叔通的 fans 兼好友给程砚秋的信:
再弟尚有一语,兄所得之钱乃血汗得来,股票不可买,不可入股,银号即利厚不可贪,弟意存入中国与兴业两行均可,千万!千万!此中事我较明白,决可负责。
读罢乐而开笑。继续看了他给程砚秋的一些书信:
假如满洲得往演唱,恐亦不能去!此即有名之人不易做人也。
可惜马连良没有一位这样的有远见的挚友! 还有新中国刚成立时的信:
以后不再是挂头牌的时代。
后来戏剧改革时期:
你以后千万对周(扬)、田(汉)、夏(衍)要谦虚,说明要他们指教……
虽只言片语,足见得此人高远。 陈叔通是清末进士,选庶吉士,后来做过商务印书馆的董事和兴业银行的董事。卒于1966年2月17日,正好是《五一六通知》前三个月,享年90岁。




